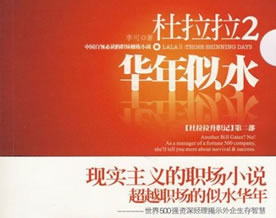这些观念,我们现在听起来简直就是无稽之谈。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古人提倡节欲保精,固然有其不科学之处,但不是提倡完全禁欲,后世有人把养生和泄欲完全对立起来,比如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为练气功而禁欲,完全是自己走上了极端。
这种直接的对立,在我国的历史上,恐怕也是站不住脚的。
如果我们有机会看一下有关的医学史就会发现,从汉魏以后,房室养生之术迅速兴旺起来,房中术的观点也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从节欲保精转为闭精纵欲。我们这里所说的闭精纵欲,就是一方面在性交中尽量不射精,另一方面尽量增多性交次数,频繁更换性交对象。根据史书记载,曹操曾向甘始、左慈等人学习房中之术,一夜曾御七十女。据房中术士们宣称,要掌握闭精之道,御女多多益善。孙思邈在《千金方》中说:“但能御十二女而不复施泻者,令人不老,有买色。若御九十三女而能自固者,年万岁矣”。他还说:“昔黄帝御一千二百女而登仙”。
闭精纵欲与节欲保精有一脉相承之处,那就是重视精液的作用,只不过闭精是从消极的避免过性生活,过渡到既过性生活,又不让精液外泻。
孙思邈在宣扬了闭精纵欲之后,又千叮咛万嘱咐道:“凡精少则病,精尽则死,不可不思,不可不慎。”
应该说,既想纵欲又想闭精,这是不容易做到的。为了做到这一点,古人总结了许多办法。比如有人提出“采气”之道,即在性交过程中深接勿动,使女性气上面热,然后以口取女气,其要诀是意动便止。还有人提出了“采战”之术,既采阴补阳,它要男方先充分引起女性性兴奋,“情动兴浓,户内滑盈溢。”然后自己“闭口咬牙,驰心物外,思念别端”,“交合之间,缓进迟退,不可躁急,勿令气喘。”
这倒是一些很好的治疗性功能障碍,提高性生活质量的技术。
如果仅从技术的角度来看,以上方法还是有效的,少动就会减少摩擦,降低对阴茎的刺激,“心念别端”就会降低或转移性中枢的兴奋,这样不射精或延长射精就可以做到了。但采气或采战之说,却实在是荒诞无稽。根据现代性医学的研究,无论是男性的精液,还是女性阴道里的分泌物,里边所含的营养物质都是很有限的,如果说通过闭精的方法来强身健体,甚至修练道行的话,分明是不明事理。
不知道古代人是如何来采精的?
在讲述采战术时,这里还有一个细节,那就是“采”的具体技术。明人洪基在《摄生总要》一书中对此有记载:“玉茎变能吸其阴精入宫,如水逆流直上。”这话听起来好象不可思议,但实际上却有可能做到。30年代时,有人曾做过公开表演,将阴茎插入一个装满水的碗里,过一段时间碗中的水就会不见了,全被他吸入了阴茎。如果把这视为一种特异功能,就不会觉得难以理解:经过一定的特殊训练,有人是不难做到这一步的。但如果把它运用到性生活中,则应该视为异端邪说,它把女性当作玩物,只顾自身,不顾他人,且不说这种方法没有实际作用,仅就其出发点而论,就是不道德的。
与采战术相联系的,古人还有“还精补脑”之说。所谓还精补脑,仍然是以“动而不泄”为原则,让未射出的精液为自身所补益。这里的补脑可以作宽泛的理解,不一定就是用精液补脑髓。在我国古代房室养生文献中,对还精补脑的方法多有记述,其要领不外乎闭口张目,紧握两手,缩鼻取气,又缩下部及吸腹,如果已有射精欲望,可用手指按会阴部,同时长吐气并啄齿。
同采战术一样,补精还脑在技术上是可以做到的,但却没有它所宣传的那种补益之处。古人中不乏明智之士,早就看到了这一点,比如明代朱丹溪、万全闪就指出:“淫精一动,皆为腐败之物,何补之有?”这个观点是符合今天人们所掌握的生理学知识的。精液虽不射出,但只能保存在内生殖器里,到一定时间就要代谢掉。这就像女性每月都要排一次卵一样,如果不能受孕,卵子就失去了价值,留着也没有用处的。
在这些方面,古人已经认识到了科学之处。应该承认,古人在房室养生方面总结出来的经验以及诸多方法,对今人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但我们不能不指出,在缺乏生理学知识的指导下,其可信程度并不很高,今人必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 2021-现在 开放平台 软著登记号:2025SR2204462 湘ICP备202200093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