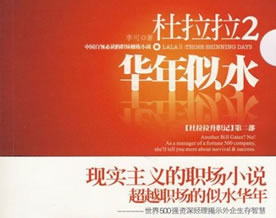回归休谟的意义
那么,在我们中国今天的语境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又具有什么意义呢?我认为在中国的现代政治理论中提出回到休谟的问题,其意义大不同于西方,与西方的现代自由主义相比,对于我们来说,回到休谟的政治哲学其内涵和意义都就更加复杂和更加重要。
首先,回到休谟的政治哲学或人性哲学,在中国的语境中意味着是对以前回到康德哲学的一种深化和提高。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正像我们前面所指出的,中国语境中的回到康德哲学,实质上乃是借助康德哲学确立一个中国化的哲学人本主义的自主价值论。然而,我们看到,这一理论成果在今天,在当今的中国社会政治理论中,已经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困难,如果说相对于启蒙主义,相对于人文化的道德热情,建立康德的哲学人本学是一种理论上的提高,那么今天中国化的康德哲学则在道德层面上停步不前了。我们知道,康德的道德哲学有其特定的历史含义,一般说来与西方传统的伦理学或政治学有所不同,是一种面向内在良知的心性哲学,因此,在它达到了人性的自主地位之后,实际上就很难对于社会政治制度问题给出深刻的说明,或者说它至少在中国的语境中并没有给出深刻的说明,并没有能够开展出一个社会的法律规则论和政治制度论,开展出一个有关自由主义的宪政理论以及政治正义论。当然,这个问题对于康德哲学本身似乎并不严重,因为康德哲学除了他的道德哲学,还有权利哲学和历史理性批判,但是,在我们的语境中所理解的回到康德哲学的含义以及所产生的理论成果及其影响,实际上最终的落实是回到了康德的道德哲学,并没有由康德的道德哲学特别是他的先验人性论,开辟出一个自由的正义规则论和社会制度论。因此,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便有可能与它们原先依据的康德哲学失去内在的本质联系,或者说中国化的康德哲学无法对中国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和宪政建设提供一个强有力的正义价值的支撑,无法催生一个面向中国式市民社会的政治哲学。
其次,与此相关,从这个角度来重新解读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重新看待20世纪以来企图用康德哲学交通中国传统儒学的理论路径,就会发现那种以康德的道德哲学来整合中国传统儒学思想的理路,实际上是很成问题的,至少是很难形成中国传统思想向现代思想的创造性转型。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康德的道德哲学与中国的儒家思想,特别是宋明理学有着某种天然的相似性,它们都属于内省的致良知的路径,都关注人的行为动机、道德善恶和内在良知等问题,从大的方面来说,都属于内圣之学。然而对于关系中国现代思想转型的触及中国传统思想命脉的由内圣开出外王的问题,康德道德哲学的作为却是有限的,从康德哲学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关联中是无法开辟出一个外王之道的,是无法展开一个面向公共社会政治领域的政制理论的,同样也无法展开一个政治德性论和正义规则论。因此在这些方面牟宗三的失败是自然而然的,李泽厚的无所作为也是可以理解的,就此而言,借助康德的道德哲学是很难实现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思想的现代性转型的。
基于上述原因,我认为,提出“回到休谟的政治哲学”这一口号,在21世纪的中国语境中致力于以休谟、斯密为代表的英国古典自由主义与中国现实社会和传统政治文化两个方面的碰撞、会通与融合,对于现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理论建设,特别是对于中国的政治自由主义,以及对于我们如何继承和发展传统的儒家思想,如何解决内圣外王之道的现代转型,其所具有的意义就远远超过了康德的道德哲学。因为休谟哲学给予我们的并不单纯是建立一种哲学的人本学,或一种致良知的道德主义,它提供给我们的乃是一个既可以塑造一种制度正义的规则理论,又可以吸取传统道德主义的美德理论。因此,在中国的语境中提出回到休谟,就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建设和接续儒家传统思想的新开展,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前景。在我看来,它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如何由人性导出一个社会的政治秩序这一问题上,休谟哲学通过它的从自然正义到人为正义的演变,为我们展示了一个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制度的理论模式,这个模式恰恰能够有效地解决传统中国的内圣开出外王的关键问题。显然,休谟开出的外王秩序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君主之道,不是一种君主的治理国家的德治模式,而是一种面向公共社会的自由政制之道,是一种以法律制度为基石的宪政模式。由此可见,休谟理论中的外王之道才是由内圣所开辟出来的真正符合现代中国的外王之道,在这方面所涉及的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显然要比康德道德哲学给予我们的理论启发大得多和丰富得多,特别是休谟政治哲学所对应着的英美社会的现实实践,所能给予我们的借鉴更是丰厚无比,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回到休谟的政治哲学,实际上又是一种将英美制度价值融会于中国传统的政治道路的选择。
第二,在如何建立一种正义规则的问题上,休谟哲学所提供的正义理论也不同于康德的道德理论,它不是基于人本主义的目的学说,也不是一种道德主义的权利正义论,而是一种基于私人财产权的规则主义的政治正义论。在我们今天中国的语境下,如果能够脱离那种人们习以为常的有关平等分配的正义观念,而开辟出一个新的在公共政治层面上的正义规则的理论,那么休谟和斯密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理论资源。在这方面,实际上休谟的理论与中国传统的思想,特别是古代孔荀的思想具有着更多的关联,而与孟子和宋明理学则隔膜较远。
第三,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休谟的人性论,他的有关自私、同情与道德情感的思想观点,为我们解读传统哲学提供了一个有别于康德哲学的新途径,而这也正是西方现代自由主义所面临的难题所在。实际上中国传统有关人性的认识与康德哲学的切合要少于与休谟哲学的切合,也就是说新儒学用康德哲学来理解和整和中国传统的道德哲学的理论路径是有偏差的,并不符合中国的现实情况。因为康德哲学最终是一个先验论的理性至上主义的道德哲学,而在中国的思想传统中,理性的先验论并不占主导地位,只是在宋明理学那里由于受到佛学心性论的影响才显得较为突出一些,而就整个儒家思想来说,它们的道德哲学实际上与休谟的道德哲学有着更大的相关性。中国思想中有关人的自私、同情、忠恕、道德情操,有关共同的利益感觉、血缘等差之爱等都曾有过非常丰富的论述,其人性论的基础与休谟的三个人性论预设有很多一致之处,而且儒家思想在相当大的方面并不是内圣的致良知路径,而是一种政治德性论,这在传统的公羊学中表现得就十分明显。孔子思想显然不是康德式的,而是休谟式的,是一种通过人性而面向社会的政治理论。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休谟哲学对于重新理解中国的儒学,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现代性转型,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总之,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中国的现代社会政治理论,对于我们整合传统的儒家思想,对于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日益艰巨的宪政建设,休谟政治哲学所具有的启发意义,所可能开辟的广阔而又现实可行的前景,都使得我们有必要重新学习与理解这位200多年前的伟大英国思想家,感受他那颗不期而然地处于三次革命巨变之间隙阶段的审慎、激荡而又平静的心灵。而这或许正是我在此提出回到休谟这一观点的意图之所在。
注释:
1 现代社群主义的另一个主将桑德尔指出:“简言之,一个由中立原则支配的社会之理想乃是自由主义的虚假应诺。它肯定个人主义的价值,却又标榜一种永远无法企及的中立性。”见《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万俊人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4页。
2 当然,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有关人性的中性学说也是一个主流的观点,甚至在儒家那里,早在孔、荀的理论中,其主导的观点认为人在本性上是自私的,或非善非恶、中性的,荀子所谓的“化性起伪”,即是指通过后天的仁义礼仪等教化人的自私本性。只是孟子一脉发扬了“浩然之气”的性善论观点,到了宋明理学,性善论才成为儒家正宗的人性理论。不过尽管如此,在儒家的中性人性论中也并没有开辟出一个公共政治社会的政治理论,其关键的原因还在于,在中国从来就缺乏一个市民社会,特别是一个西方近代的以市民阶级为主体的经济社会,因此也就形成不了一种独立公正的基于私人财产权的法律制度。
3 我在《法律秩序与自由正义——哈耶克的法律与宪政思想》一书中,通过分析“正当行为规则”对于哈耶克整个社会政治理论的极端重要意义,所力图说明的也正是哈耶克在这个问题上所具有的重要贡献。参见拙著第一、三、六章的有关论述。
4 参见《追寻美德》,第17章。
5 参见《追寻美德》,第14章。
6 《法律帝国》,李常青译,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5页。不过,也应该指出,德沃金有关法律与博爱关系的论述又具有着很深的法国思想的印记,可以说他的博爱原则是从法国思想中提炼出来的,尽管非常高尚,非常具有理想性和感染力,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只是一种非常抽象的观念,而非真正的自然情感,因此,与休谟和斯密意义上的包含了人的自私与同情的道德感还是有相当大的距离的。尽管如此,我们也应该看到,德沃金的这种努力至少说明了现代的政治自由主义有一种对于传统德性思想的回归,有一种企图克服法律的纯形式而向包含着人情的正义德性的回归。只不过这种回归如果能够放弃那种法国式的意识形态化了的博爱原则,进而转向英国古典思想的道德同情,也许更能揭示现代政治自由主义所应回归的路径。
7 参见Johy Gray ,Hayek on liberty , Third edition ,Routledge,1998,p.4. Chandran Kukathas,Hayek and modern liberalism,preface.,Oxford,1989.拙著《法律秩序与自由正义——哈耶克的法律与宪政思想》,第三章。
8 参见《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三章。
9 对此,李泽厚曾经有过深入的论述,他写道:“康德哲学的巨大功绩在于,他超过了也优越于以前的一切唯物论者和唯心论者,第一次全面地提出了这个主体性问题,康德哲学的价值和意义主要不在他的‘物自体’有多少唯物主义的成分和内容,而在于他的这套先验论体系,因为正是这套体系把人性(也就是人类的主体性)非常突出地提了出来。”见“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载《论康德黑格尔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
10 参见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11 《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5页。
12《反自由主义剖析》,第150页。斯图沃特分析道:“对于休谟来说,奴隶制虽是历史事实,但它是野蛮的。市民社会由个人组成,他们所有的人都是参与者,奴隶制与市民社会的理念则是格格不入的。”“休谟指出,奴隶制是古代经济与现代经济的最主要的不同,奴隶制不仅是悲惨的,也是不人道的。”见Stewart,The Mor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David Hume, p.186.p.266.另参见David Hume Political Essays,Editer by Knud haakonsse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Introduction, 休谟在“论古代国家的人口稠密”一文中“指出,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奴隶制,它不仅是野蛮的制度,而且与现代的雇佣劳动相比,不利于人口的增长。”
© 2021-现在 开放平台 软著登记号:2025SR2204462 湘ICP备202200093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