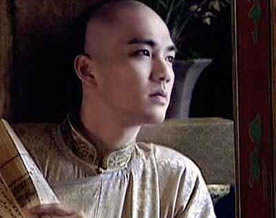六、形而上学哲学的终结,与其自身的书写方式相关。叔本华的后期哲学,与康德和黑格尔比较起来,更具有散文的味道,正是在叔本华的笔下,哲学的书写开始脱离了理性和逻辑的概念语言,因此哲学才开始进入到了大众的视野,而不是在学术研究的活动中流通。形而上学哲学因为其研究的对象是抽象的,形式是思辩的,与我们的生活世界是相距甚远。因此它只能存在于学者的研究之中,与大众的绝缘的。蒙田和梭罗的哲理散文,永远会比笛卡儿和康德的哲学读者多。形而上学哲学是通过大学里的知识精英来影响一个时代文化的,这是一种只能自上而下撒播的思想。形而上学哲学所解决的问题是天上的,而不是人间的,绝对精神的运动,对于每一个在现实中生活着的人,是遥不可及的,犹如夜空中的一颗遥远的星,虽然明亮,但却不如离我们更近的月亮亲切。
叔本华在晚年收获到了他应得的荣誉,他的荣誉来自各个阶层的自由读者,而不是学院,黑格尔在学院中永远比叔本华更受欢迎,直至今天也是如此。尼采深受叔本华的影响,他在哲学的书写方式上,完全采取了修辞的方式,言简意赅的格言警句,彻底的颠覆了形而上学的逻辑体系语言。他既是一个哲学家,也是一位诗人,尽管他是以哲学闻名于世的,但他自己更喜欢别人把他当作一个艺术家。尼采的哲学,公然宣称:“我们正因为有艺术,才不致毁灭于真理。”尼采的第一部哲学著作《悲剧的诞生》,更像一部美学著作。实际上这本书对20世纪的美学产生的影响也是难以估量的。尼采的哲学不仅在书写上,也在命题上转换了哲学的方向,强力意志、永恒轮回、超人,与自柏拉图以来的形而上学所讨论的东西完全不同,尼采对本体论的兴趣来源于对人生存本身的思考。形而上学将其研究指向世界和终极实体,而尼采却将他的思考指向人和生存的此在。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的哲学之中,人的生存本身成为哲学的中心事件。自柏拉图以来的形而上学,关心理念、上帝、物自体、绝对精神,惟独没有将目光落在人及其此在生存上面,形而上学将目光盯住抽象枯燥的概念和逻辑,却偏偏遗忘了活生生的人本身。
笛卡儿从“我思故我在”中欣喜的发现了近代哲学的第一原则,但他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我思”之前,首先有一个活生生的人存在,一块石头是不会“我思”的。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尼采都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正是因为他们的哲学才把人的生存作为哲学的命题,或许哲学最初也是关心人的生存问题的,但那是在柏拉图以前,而不是形而上学主宰哲学的时代。尼采的哲学中虽然有世界观——永恒轮回,本体论——强力意志,但他的哲学核心却是一个问题:人应该怎样生存。尼采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超人”。或许我们不应该称其为概念,它是指向人的生存的。尼采不会为人们再像形而上学那样设置一个永恒的终极目标,超人只能存在于生成和创造之中,在抽象的哲学思辩中是永远找不到超人“是什么”的答案的,而当你跟随酒神狄奥尼索斯的歌队,心醉神迷的起舞时,或许超人的闪电会在你心中一闪而过。
尼采之后的20世纪,出现了诸如现象学、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哲学流派,这些哲学都是沿着反理性和形而上学的道路前行的,我们可以说,这是一股泛存在主义哲学潮流,人在世界中的生存问题,成为这股哲学思潮的核心。这些哲学摈弃了形而上学的抽象思维,开始为具体的人类生存问题寻找出路,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让哲学家们在巨大的危机感中,不得不把人类的生存本身作为其思考的中心。因为以往的任何时代,人类都没有像这个时代一样的对自身的前途充满忧心和绝望,哲学家不得不担当起为人类的未来寻找出路的任务,尽管他们力不从心,但只能不得已而为之。
七、尼采和马克思在19世纪末就开始担当起了这样的人类导师角色,尼采的哲学更像是先知的启示录,尽管他不想让人们把他看成先知。但他的《查拉图斯他拉如是说》本身,却包含了明显的启示意图。因此有人把他称为酒神弥赛亚主义者,像尼采这样的酒神弥赛亚主义者不只他一个,在他之前的18世纪有诗人荷尔德林,在他之后的20世纪有海德格尔。这三个人同时也可以被称“诗人思想家”。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偶然的,尼采哲学中的酒神精神,是否受到荷尔德林等德国浪漫派诗人的影响很难说,但他们对酒神和古希腊悲剧精神的推崇,却是相同的。而他们都对海德格尔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对他后期关于对世界黑夜和技术时代的思考。
荷尔德林、尼采和海德格尔思想之间的亲缘性,不仅仅在于他们之间有一种相互影响和传承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都出自一个源头,柏拉图以前的古希腊文化。那是一个比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从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更久远更丰富的文化——在荷马史诗,宗教仪式和古典悲剧,以及雅典和斯巴达人的生存方式之中。古希腊哲学出现的本身,就意味着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相互融合照耀的古典文化开始走向衰落,在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中,古老的真理火种还在燃烧,巴门尼德还能说出:“思想与存在是同一的。”这样的话来。柏拉图的哲学中至少还保留着对话的鲜活性,亚里士多德的“实体”、逻辑和形而上学,彻底的导致了古希腊文化灵性的丧失,永恒燃烧的活火,变成了抽象的逻辑概念。
哲学,或者说形而上学的出现,实质上是真理不再能被人经验到之后,出于对失落的真理的追寻的一种产物。在诸神显现的时代,人们依靠信仰接近真理,在诸神隐退的世界,人们依靠怀疑来追求真理。在没有神的世界黑夜时代,有谁还能记挂着神的曾在和未来的将到呢?在中世纪的人们心中还有信仰,在文艺复兴的人们心中还有虔诚,在古典时代的人们心中还有敬畏,思想启蒙和法国大革命之后,近代的理性原则,科学观念和政治制度,彻底的在西方文化中取得了统治地位。现代人突然发现,自由美好的理性王国没有如期而至,但曾经有过的信仰、温情和家园,都已经被现代工业技术和金钱利益观连根拔起。感伤主义开始在欧洲大地上蔓延,浪漫主义诗人如涕血的夜莺,歌唱往昔中世纪的美好田园生活,这正是荷尔德林出现的时代。尽管受到席勒的赏识,但他的诗歌却没有在当时得到人们的重视。因为他的诗歌太古老,或者说过于超前了。
“荷尔德林是贫困时代诗人的先行者。因此之故,这个世界时代的任何诗人都超不过荷尔德林。但先行者并没有消失于未来;不如说,他出于未来而到达,而且,唯有在他的词语之到达中,未来才现身在场。……那种看法——即认为,唯当有朝一日‘全世界’都听到他的诗歌时,荷尔德林的时代才会到来——恐怕是错误的。在这种畸形的看法中,荷尔德林的时代是永远不会到来的。因为,正是世界时代自身的贫困给世界时代提供了力量,凭这种力量,它——不知其所为地——阻碍荷尔德林的诗成为合乎时代的诗。先行者是不可超越的,同样地,他也不会消逝。因为他的诗作始终保持为一个曾在的东西(einGe-wesenes)到达的本质因素把自身聚集起来,返回到命运之中。”海德格尔的这段话,怎么听来都不像在论说一位诗人,而是在谈论一位先知。一个疯了的诗人,怎么会成为一位先知呢?这不是十分荒谬的事情吗?
从卡珊德拉和拉奥孔的古老年代起,有哪位先知所说的预言,不是被当作疯言疯语而被一些无知的人加以嘲弄呢?所有先知的祖先是普罗米修斯,他曾警告他的弟弟,不要接受天神的礼物,但他的弟弟是后觉,也就是在事情发生之后才发觉事情之本相的人,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时,他才知道普罗米修斯的话是什么意思。我们今天完全可以把这当成神话传说,但却没有深思其中所包含的真理。就像当年将特洛伊人面对卡珊德拉的警告一样,因为现代人只相信经验理性和科学真理。
© 2021-现在 开放平台 软著登记号:2025SR2204462 湘ICP备2022000939号|